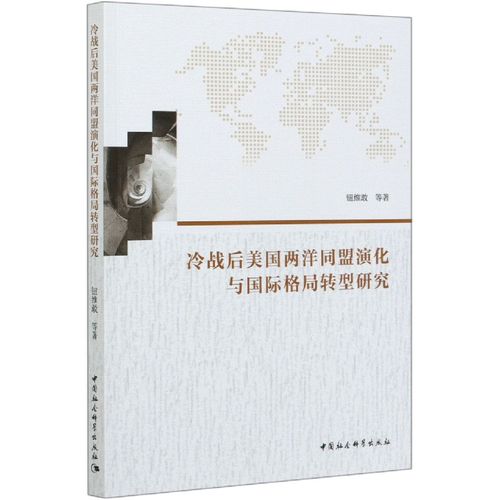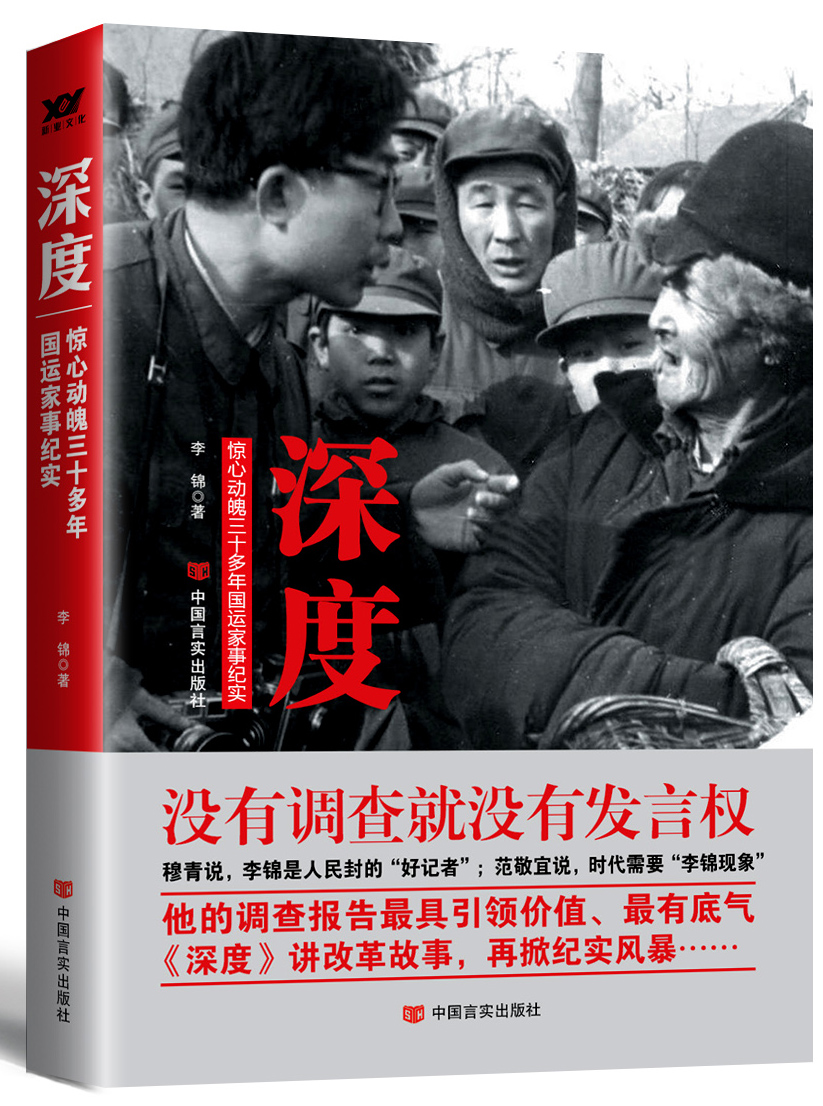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出现了深刻的错误,而我们似乎无法想象另一种可能。”
这是他的核心理念:
如今我们带着先入之见来回顾20世纪,将它看作一个政治极端、悲剧性错误、方向选择错误的时代,一个谬误的时代,谢天谢地,我们现在从那里走了出来。但是我们现在就不会陷入谬误了吗?我们改为膜拜私有部门和市场,不就是简单地逆转上一代人对“公有制”和“国家”或“计划”的信念吗?说到底,主张一切事务和政策(无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必须依靠全球化经济, 它那无法避免的法则,以及它那贪得无厌的需求,这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确,这种对经济必然性及其铁的法则的崇拜,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核心的前提。
也因此,人们在扬弃左翼思想时,也不应该跌入市场膜拜的教条中,更不该让社会民主的理念与苏东式的模式一起进入历史的尘埃。
社会民主曾经在战后的世界,提供西方一个经济稳定、社会相对平等、政治民主的体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进行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如今这一切都瓦解了。
而要进行社会民主计划,首先必须再一次学会“思考国家”,并解除西方根据冷战的胜利而产生的偏见。
尤其,“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期上的信任和相互依赖。”(《沉疴遍地》,第7页)面对这些恐惧与不确定,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包括提供的社会服务,更为重要,“对我来说,恐惧的重新出现,和其政治后果,是支持社会民主最有力的论证。”
《沉疴遍地》或者朱特的社会民主思想,在当下是特别具有意义的。他对现实思考的重新出发点是后冷战时代。进入1990年代之后,如同西方,中国市场力量变大了(但当然是中国特色的),民间出现对自由市场的崇拜和大批哈耶克的信徒,希望政府越小越好。一如朱特所提及,“东欧年轻人误认为经济自由和干预性国家是互相排斥的”。虽然事实上,国家对市场的某种介入并不必然代表减少人们的经济自由,乃至政治自由(可以参见周保松就“市场、金钱与自由”主题的系列文章)。
但自由派的担忧与欲望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当下的现实就是国家掌握着巨大经济资源,自由市场派担心一旦主张扩大国家在管制市场和介入重分配上的职能,只会扩大国家的权力,壮大背后那只掌握国家机器的政治之手。
另一方面,左翼的语言又被老左与新左派所绑架,缺乏进步性。尤其在九十年代谈强化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具有社会学和现实上的意义,但不幸的是,这些提倡者最终被证明是支持体制的新国家主义者。
于是中国似乎只有国家左派与自由市场派两种主要叙事。
在西方,朱特说,“当代对经济自由的崇拜,结合日益增加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只会导致降低社会服务和减少经济管制,但却会伴随着政府对通信、运动和舆论的监控。这是西方形式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提法非常有意思,但却未必对,因为中国的现实并不是如此;西方形式的和东方形式的还是有巨大差别。
但无论如何,朱特期待的“重新思考国家”,是以政治自由为前提:“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与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将是有益的。”
即使人们不再相信乌托邦,但是也不能让市场决定一切资源的分配、组织我们的公共生活。国家对市场的管制,和进行再分配来维持社会团结是重要的,但这样的国家体制必须被制衡、被监督。朱特说,西方社会民主的困境之一是,由于极权主义已经消失,所以强调民主是多余的。“如今我们都是民主派了。” (《沉疴遍地》, 104页)
声明:本媒体部分图片、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025-84707368。